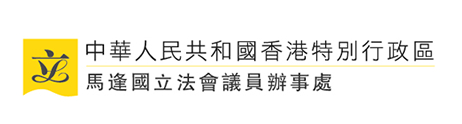發言
返回
法案:《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02.06.2016
主席,《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條例》”)於2006年8月制定,目的是訂立法定的機制,規管執法機關所採取的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以求在防止和偵測嚴重罪行和保障公眾安全,以及在保障私隱和其他個人權利兩者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
政府也就此委任了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專員”),以監督香港警務處、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及廉政公署4個執法機關,在進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時是否遵從《條例》所訂的規定。專員亦會就其監督工作,每年向行政長官提交周年報告,並提出完善監督機制的建議。
首任專員胡國興法官及次任專員邵德煒法官在其提交的周年報告中,都曾提出希望政府能修訂《條例》,賦予專員權力,查核受保護的成果,讓專員可以查明涉案人員的解釋是否真確,好讓他們更好地發揮專員的監督功能。
今次的《 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 (修 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正是回應專員的建議,修訂法例,賦予專員及其屬下人員明確的權力,檢查、檢視及聆聽受保護成果,包括關乎違規情況或異常事件的受保護成果、涉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或新聞材料個案的受保護成果,以及專員隨機抽查其他個案的受保護成果。
我認同政府應修訂《條例》,賦予專員權力,以期更好地履行其監督的工作。然而,我亦非常關注,在賦予專員查核受保護成果的同時,如何保護該等受保護的成果不致外泄,以及有何措施監督專員屬下人員在獲轉授權力接觸保護成果期間,不會出現導致有關資料外泄的風險。
雖然政府回應指出,專員及其獲轉授權力的人員,只會在執法機關內的處所進行檢查、檢視及聆聽受保護成果的工作,受保護的成果不會被轉移或複製,而在審查期間所進行的書面紀錄或摘要,均有銷毀的機制,因此資料外泄風險已大大降低。同時,專員辦事處內獲轉授權力的所有可接觸敏感資料的人員,均須接受政府內部最高級別的操守審查。專員亦指出,在條例草案通過後,便會訂立內部指引,詳細列明進一步保障措施,以防止有人未獲授權取用和披露受保護成果。
不過,我們也必須明白,該等受保護成果,不單可能涉及新聞材料和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等敏感資料,也可能包括一些個人私隱,或是一些可能會影響執法機關的截取或監察行動的資訊。因此,在處理這些敏感資料時,必須慎之又慎,任何有外泄資料的風險,我們都不能疏忽。
我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專員能夠盡快制訂內部指引,訂立專員在查核受保護成果的機制,列明保護有關資料的措施,並訂明專員辦事處人員在未獲授權取用和披露受保護成果,而需面對的內部懲處的機制,以確保敏感資料不被外泄。我更希望這些措施和指引能足以令大家放心。至於專員查核受保護成果的工作,也應在周年報告作適當的匯報和交代,讓議會及公眾了解專員有關的工作。
主席,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另一個受關注的重點是,現時的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是否應包括在《條例》規管的範圍內,當中的爭議,主要是《條例》內有關“截取”、“截取行為”及“通訊”三者的定義。
根據《條例》,“截取”就是指就某項通訊而進行任何截取作為,如有關通訊是藉電訊系統傳送,而執法機關在傳送的過程中截取這些通訊,便屬於《條例》下的“截取作為”。所謂的“電訊系統”一詞在該條例的涵義,即“藉導向電磁能或無導向電導向電磁能或藉此二者而傳送通訊的電訊裝置或連串裝置”。
我認為,就“電訊系統”所表述的範圍,已包含了社會上大部分通訊的模式。因此,《條例》下“截取”、“截取行為”及“通訊”三者的定義,涵蓋範圍已相當廣泛和清晰。況且,科技日益進步,社會通訊的渠道日新月異,我們不難想像現時我們所用的通訊方法,過了一段時間或數年後,就已經被淘汰。因此,法例的定義需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避免需要經常修訂。因此,為特定的通訊方式訂立規管,我認為並無必要。
至於從互聯網供應商伺服器取得資料,一般是由執法機關根據相關條例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後才能進行,而這與《條例》規管的截取及秘密監察行動的性質,也有一定的差別。我認為委員如對此問題仍然關注,應在相關事務委員會跟進,而不需要在現階段納入此條例草案內。
主席,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部分委員認為,應向不遵從專員要求的執法人員施加刑事制裁。涂謹申議員亦就此動議修正案,訂明銷毀提供予專員的受保護成果,即屬犯罪,最高可判監兩年。
現時,如執法機關人員沒有遵守《條例》或《實務守則》的規定,是需要接受紀律處分的。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自《條例》生效以來,便有超過60人因此而受到紀律處分。根據歷年專員撰寫的周年報告,兩任專員整體上均滿意執法人員的表現,違規或異常情況的出現,都不是因為執法人員惡意或蓄意不遵守或不理會法定條文或法例所導致。若執法人員故意在沒有訂明授權的情況下進行截取或秘密監察,可以根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作出起訴,最高可判監7年。因此,無論是輕微的違規或是嚴重的個案,法例上其實已有一定的懲處機制。
此外,政府亦指出,為截聽的條例引入刑事懲處,需與相關政策局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有關規管非公職人員進行截取或秘密監察行為的建議所作的檢討,一併作全盤考慮。故此,我認為並不急需於在本立法年度內,為截聽的條例引入刑事制裁,有關安排可於稍後與其他相關檢討一併處理。
主席,《條例》實施了接近10年,對偵查嚴重罪案及完善公眾安全的保障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專員的監督和提供建議改善的情況下,規管的機制一直不斷完善當中。雖然每年大約有10宗的違規及異常情況,但整體而言,我認為《條例》的實施仍屬暢順。當然,我希望政府當局及執法機關在未來的日子裏,能切實落實專員的建議,加強執法人員的相關培訓,將違規情況減至最低。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政府也就此委任了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專員”),以監督香港警務處、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及廉政公署4個執法機關,在進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時是否遵從《條例》所訂的規定。專員亦會就其監督工作,每年向行政長官提交周年報告,並提出完善監督機制的建議。
首任專員胡國興法官及次任專員邵德煒法官在其提交的周年報告中,都曾提出希望政府能修訂《條例》,賦予專員權力,查核受保護的成果,讓專員可以查明涉案人員的解釋是否真確,好讓他們更好地發揮專員的監督功能。
今次的《 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 (修 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正是回應專員的建議,修訂法例,賦予專員及其屬下人員明確的權力,檢查、檢視及聆聽受保護成果,包括關乎違規情況或異常事件的受保護成果、涉及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或新聞材料個案的受保護成果,以及專員隨機抽查其他個案的受保護成果。
我認同政府應修訂《條例》,賦予專員權力,以期更好地履行其監督的工作。然而,我亦非常關注,在賦予專員查核受保護成果的同時,如何保護該等受保護的成果不致外泄,以及有何措施監督專員屬下人員在獲轉授權力接觸保護成果期間,不會出現導致有關資料外泄的風險。
雖然政府回應指出,專員及其獲轉授權力的人員,只會在執法機關內的處所進行檢查、檢視及聆聽受保護成果的工作,受保護的成果不會被轉移或複製,而在審查期間所進行的書面紀錄或摘要,均有銷毀的機制,因此資料外泄風險已大大降低。同時,專員辦事處內獲轉授權力的所有可接觸敏感資料的人員,均須接受政府內部最高級別的操守審查。專員亦指出,在條例草案通過後,便會訂立內部指引,詳細列明進一步保障措施,以防止有人未獲授權取用和披露受保護成果。
不過,我們也必須明白,該等受保護成果,不單可能涉及新聞材料和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等敏感資料,也可能包括一些個人私隱,或是一些可能會影響執法機關的截取或監察行動的資訊。因此,在處理這些敏感資料時,必須慎之又慎,任何有外泄資料的風險,我們都不能疏忽。
我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專員能夠盡快制訂內部指引,訂立專員在查核受保護成果的機制,列明保護有關資料的措施,並訂明專員辦事處人員在未獲授權取用和披露受保護成果,而需面對的內部懲處的機制,以確保敏感資料不被外泄。我更希望這些措施和指引能足以令大家放心。至於專員查核受保護成果的工作,也應在周年報告作適當的匯報和交代,讓議會及公眾了解專員有關的工作。
主席,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另一個受關注的重點是,現時的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是否應包括在《條例》規管的範圍內,當中的爭議,主要是《條例》內有關“截取”、“截取行為”及“通訊”三者的定義。
根據《條例》,“截取”就是指就某項通訊而進行任何截取作為,如有關通訊是藉電訊系統傳送,而執法機關在傳送的過程中截取這些通訊,便屬於《條例》下的“截取作為”。所謂的“電訊系統”一詞在該條例的涵義,即“藉導向電磁能或無導向電導向電磁能或藉此二者而傳送通訊的電訊裝置或連串裝置”。
我認為,就“電訊系統”所表述的範圍,已包含了社會上大部分通訊的模式。因此,《條例》下“截取”、“截取行為”及“通訊”三者的定義,涵蓋範圍已相當廣泛和清晰。況且,科技日益進步,社會通訊的渠道日新月異,我們不難想像現時我們所用的通訊方法,過了一段時間或數年後,就已經被淘汰。因此,法例的定義需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避免需要經常修訂。因此,為特定的通訊方式訂立規管,我認為並無必要。
至於從互聯網供應商伺服器取得資料,一般是由執法機關根據相關條例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後才能進行,而這與《條例》規管的截取及秘密監察行動的性質,也有一定的差別。我認為委員如對此問題仍然關注,應在相關事務委員會跟進,而不需要在現階段納入此條例草案內。
主席,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期間,部分委員認為,應向不遵從專員要求的執法人員施加刑事制裁。涂謹申議員亦就此動議修正案,訂明銷毀提供予專員的受保護成果,即屬犯罪,最高可判監兩年。
現時,如執法機關人員沒有遵守《條例》或《實務守則》的規定,是需要接受紀律處分的。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自《條例》生效以來,便有超過60人因此而受到紀律處分。根據歷年專員撰寫的周年報告,兩任專員整體上均滿意執法人員的表現,違規或異常情況的出現,都不是因為執法人員惡意或蓄意不遵守或不理會法定條文或法例所導致。若執法人員故意在沒有訂明授權的情況下進行截取或秘密監察,可以根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作出起訴,最高可判監7年。因此,無論是輕微的違規或是嚴重的個案,法例上其實已有一定的懲處機制。
此外,政府亦指出,為截聽的條例引入刑事懲處,需與相關政策局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有關規管非公職人員進行截取或秘密監察行為的建議所作的檢討,一併作全盤考慮。故此,我認為並不急需於在本立法年度內,為截聽的條例引入刑事制裁,有關安排可於稍後與其他相關檢討一併處理。
主席,《條例》實施了接近10年,對偵查嚴重罪案及完善公眾安全的保障工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專員的監督和提供建議改善的情況下,規管的機制一直不斷完善當中。雖然每年大約有10宗的違規及異常情況,但整體而言,我認為《條例》的實施仍屬暢順。當然,我希望政府當局及執法機關在未來的日子裏,能切實落實專員的建議,加強執法人員的相關培訓,將違規情況減至最低。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