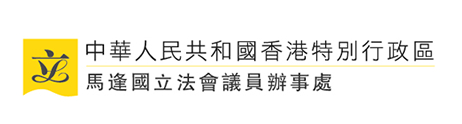主席,香港的稅收結構畸形,340萬勞動人口之中,只有大約120萬人需要繳納薪俸稅,而當中九成五的薪俸稅由50萬名納稅人繳交。小部分人交大部分的稅,政府的收入易受經濟因素影響,波幅極大。另一方面,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令勞動人口減少,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公共開支持續膨脹。雖然我們有較豐厚的盈餘,有條件提供一些短期的稅務優惠,但在這個客觀的人口和經濟條件下,我不禁要問:我們還有空間、還有條件去談全面減稅嗎?
環顧全球,香港是少數維持低稅率的地方,個人入息稅及公司利得稅的標準稅率分別是15%及16.5%。相比起鄰近實行累進式稅制的國家及地區,例如南韓、日本和中國內地等,邊際稅率最高可達40%,甚至50%,我們的稅率已經十分低。加上政府每年在稅項的慣性寬免措施,使其收入相當依重賣地收入的幫補。剛發表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亦提及,在人口老化及出生率低的情況下,勞動人口將會於2018年開始逐步減少,可能會令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可以預期個人入息稅及利得稅收入亦會進一步減少,稅基亦會更為狹窄。
如果收入少,而支出不多,問題相對不大。但事實卻是公共開支膨脹的趨勢持續,根本難以逆轉。由於種種原因,用於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等方面的開支正逐步增加,也會繼續增加。例如政府估計,如果不進行醫療改革,到2033年,可能有一半的稅收要用作醫療服務開支,加上人口老化帶來的開支和其他支出,更有機會入不敷支。
令問題更嚴重的是近年市民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有人擔心香港民粹主義、福利主義日漸高漲,政黨和市民可以不問成本提出很多要求,期望政府在方方面面給予更多支援,減輕財政負擔。全民退休保障、15年免費教育、增建公營房屋等涉及龐大財政資源的訴求與日俱增,但錢從何來的問題,卻很少人去想。
我並非要否定社會有上述的需要,也並非說不應紓緩市民的財政壓力,但從理性角度看,全面減稅會嚴重影響香港公共財政的持續性和健康。如果既要落實各項新的社會投資,又要全面減稅,事實上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社會必須有所抉擇。
我認為要紓緩市民的財政壓力,又要加大社會投資的話,比較可行的做法是從3方面着手。首先是檢討目前的稅制,令稅制更多元化,引導社會在這方面作理性的討論,以建立一個更公平、更穩定,更具持續性的稅制,令我們的公共財政更健康。
其次,在有穩定的稅制及更穩定的稅收的前提下,運用財政盈餘規劃長遠政策,加大在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的社會投資,為社會帶來更大的效益。同時,亦應利用稅制政策和公共開支去促進經濟發展,開拓新的領域,提高香港長遠競爭力,將公共開支轉化成社會資產。
最後,應推行針對性的減稅措施,並為推動長遠政策提供誘因,代替全面減稅。鑒於香港的中產要繳納薪俸稅之餘,又沒有享用大部分社會福利。數次的金融和地產危機,導致香港出現中產階層向下流動的趨勢,面對工時長、職業欠缺穩定性、安全感低、生活壓力加大所帶來的財政壓力,他們理應受到政府關注。事實上,我所屬的新世紀論壇近年一直要求政府為中產提供稅務優惠和支援,增設私人醫療保險,私人樓宇租金、大廈維修及子女教育等數項有上限的免稅額,以減輕中產的稅務負擔。
主席,基於上述原因,我並不認同香港現時有條件實行全面減稅,故此,我無法支持謝偉俊議員的原議案及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有些同事的修正案要求政府檢討稅制,維持政府穩健的財政收入、善用財政盈餘及透過針對性的稅務措施,減輕中、下階層市民的稅務負擔。這些建議與我的理念比較相近,故此,我會支持梁繼昌議員、林健鋒議員、姚思榮議員及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至於其餘的修正案,雖然我不是完全否定在現階段新增稅項及“能者多付”的原則,但如果在現階段落實,可能會加重市民的稅務負擔,較具爭議性。我認為應該留待社會進一步討論,在有共識的時候才實行,因此,我較難支持這些修正案。